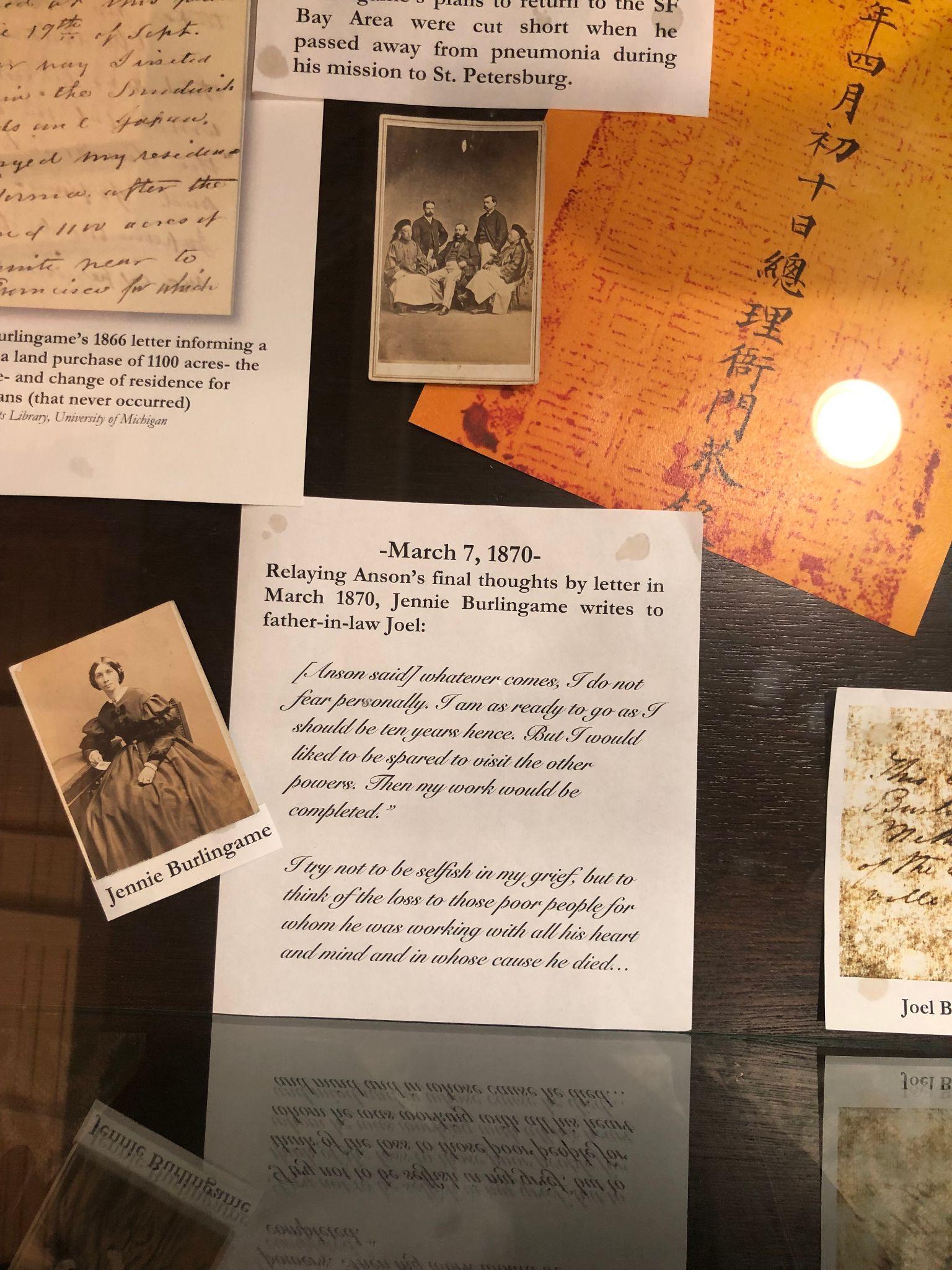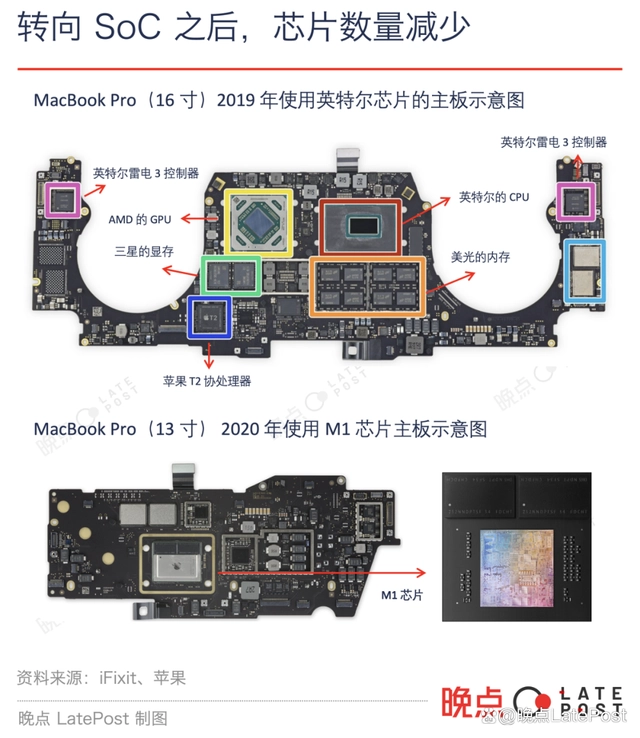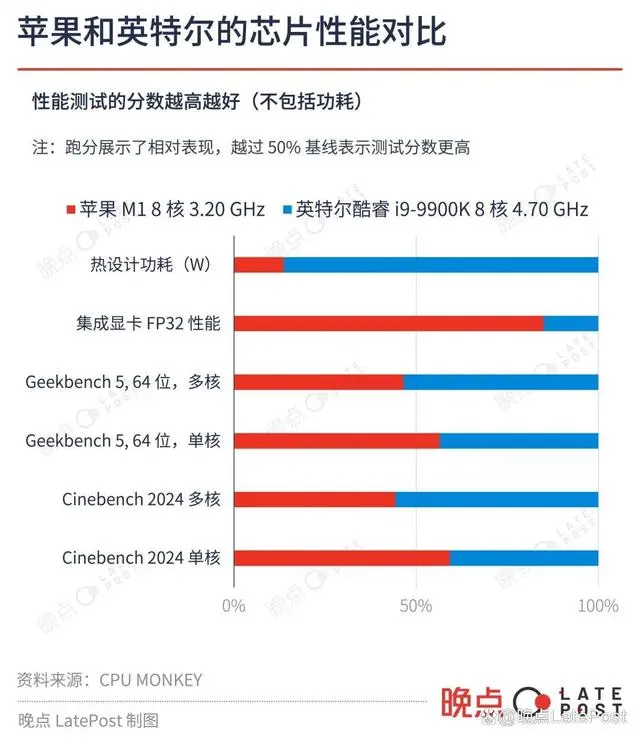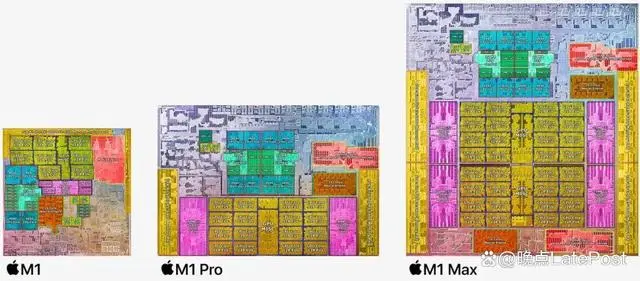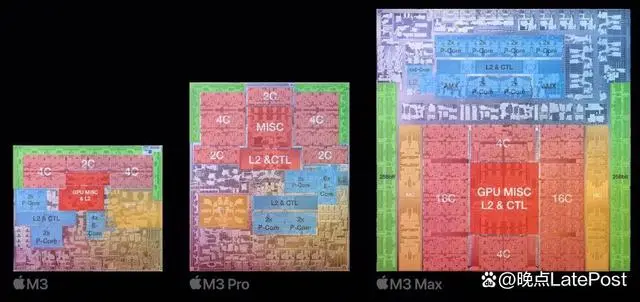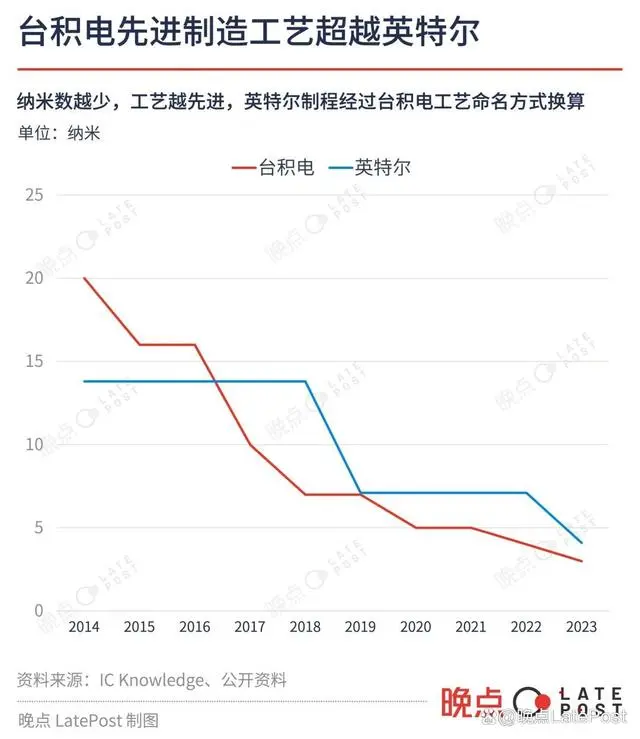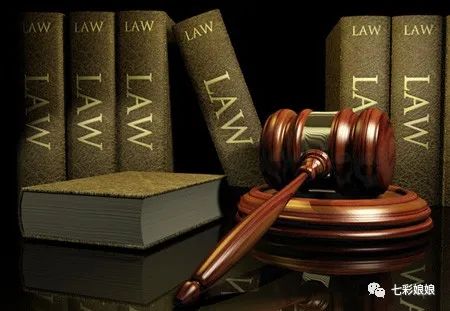作者: 罗新
2023年10月25日,中午12点20分,我坐在美国新泽西的博根郡法院331法庭的被告席上。我的心脏怦怦地跳,仿佛要跳出胸口。屋子里的温度很低,我紧握的双手却似乎有了汗意。
刚刚,女法官宣布,陪审团已经做出裁决,即将宣布结果。
这场长达四年之久,并且耗费了我们无数心神精力的荒唐官司,到底结局如何,就要揭晓。
七位陪审员鱼贯而入,为首的一个年轻小伙子手里拿着一张纸。他是一号陪审员,那张纸上就是裁决结果。
陪审员都落座后,女法官询问小伙子:“陪审团做出裁决结果了吗?”
“是的。”
“好的,请回答我的问题:原告白兹先生是否被XX公司拒绝了申请工作的机会?”
“没有。”
“投票结果是什么?”
“7:0。”
我的大脑似乎有烟花绽放。我们赢了!
7:0,压倒性的胜利!
面对咄咄逼人的大牌律师团,我就像一个打不死的小强,硬扛到今天,终于让对方一败涂地。
一、碰瓷
事情要从四年前说起。
我和家人在博根郡开了一个小店。2019年圣诞节前夕,我收到一份厚厚的法庭文件。打开一看,发现我们被人告了。原告是一个西班牙裔的69岁的老人。他说他是我们店的常客。在2019年3月30日,他看见我们店的门上贴了一个招聘启事,他就走了进去,向一个非裔主管申请工作。但是这个非裔主管却说:“不,你太老了”,然后还加了一句西班牙语:“太老了”。老头就离开了。
他指控我们对他有年龄歧视的违法行为,并以此找了律师,到新泽西高级法院把我们告了。
厚厚的文件里都是他的律师写的冗长的法律条款,要求我们提供一切相关证据,甚至包括所有社交媒体的信息等等。
突然之间成了被告,我有点懵。按照指控,这件事发生在差不多9个月前,但是我和几个家人都一无所知。店里的确有个黑人员工安东尼,但是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员工,不是主管。
打电话问安东尼是否有这个事情,他一口否认,还说:我怎么能说这个话,招聘这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干嘛要去得罪人。
他是我们的老员工,平时也不是那种喜欢得罪人的性子,而且他就是普通店员,招聘的事的确不关他的事。
我们被碰瓷了!
我开始在网上搜索这类案件。控告职场年龄歧视的案件有很多,比如有些公司解雇年龄大的员工;比如有些公司在录取的时候,选择了年纪轻的候选人。
我大概有了点底。第一,我们店里没有“非裔主管”;第二,唯一的黑人员工否认说过这句话;第三,这个人没有递交简历,没有被面谈,没有在我们店里工作过一天。第四,我和家人们作为这个店的主人和管理者,从来不知道这件事发生过。
冤,真冤,比窦娥还冤!但是,事情砸自己头上了,只能去应对。于是,我和家人去寻找律师,从此踏上一条长达四年之久的应诉之路。
二、律师A
第一个律师A是一个大约60来岁的白人。他是由我们认识的另一个律师推荐的,是专门负责劳动法这方面的律师。
2020年的元旦刚过,我们就在他的律师事务所见面。他听了整个情况后说:我经常是替被歧视一方打官司,如果这个人找到我,我是不会接这个案子的。第一,案子的证据太单薄,基本上就是他的自述。第二,即使是打到最后他赢了,也最多赔他几个月的工资,作为律师,根本没多大油水。
他说很多情况下,面对这类案子,被告的一方出点钱,早早了结就好。
这也是后来几乎所有的律师,以及所有知道这个事情的人,给我们的建议。
在美国,打官司是一个漫长而昂贵的过程,快速和解,是最经济的做法。
当然,这个时候还不到和解的阶段。律师A接下这个案子,开始回应对方。他的费用是每个小时400美元。
我们一开始想的有点简单:原告指控一个“非裔主管”拒绝了他的工作申请,我们根本没有“非裔主管”,所以他的指控不成立,这事就应该到此为止了。
双方律师开始索要材料,进行取证。这时候,我们的律师犯了第一个错误,他没有向法庭提交撤案动议(motion to dismiss)。虽然提交了动议也不一定能被批准,但是至少要尝试一下。这个案子的情况并不复杂,遇到某个法官也许就直接撤案了。
到了1月底,新冠在中国爆发,我和许多华人一样,开始往国内运送各种医疗物资。3月份,新冠在美国也爆发了,我们又开始打下半场。疫情在美国愈演愈烈,我们也关店了。
三、开价
6月初,我们收到了对方律师的第一次开价,要求我们赔偿原告4万5千美元的经济和精神损失。并说:如果你们继续打下去,你们会轻易花掉十万美元以上的费用。
4万5千美元,对于我们这样的小生意来说,虽不是天文数字,却依然很多,特别是我们正在关店期间,没有了收入。
而从我们的心理层面上看,这个数字就被放大了十倍、百倍。我们没有违反法律,我们连你是谁都不知道,谈何歧视?给你几千元,把你打发走,我们可以勉强接受。赔你$45000,凭什么?你说你有精神损失,我们因为这个案件,也很焦虑,精神损失更大!
我和家人决定:不去讨价还价,把官司打下去。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
就这样,双方律师你来我往,索要各种证据、填写各种文件。我们也不断收到律师费用。每个小时$400,随便几个电话,几封邮件,钱就哗哗地流出去了。
律师A说把所有程序打完,我们大约需要2万5到3万美元。我问了几个华人律师朋友,他们也说这个价格差不多。
八月份,对方律师大概看到疫情还遥遥无期,大量的小企业受到严重影响,我们店也在关门中,觉得让我们吐出4.5万也困难,发了邮件,把赔款降到了2.5万美金。他们是这样说的:假如你们打下去,即使庭审赢了,$25000只相当于你们支付的律师费的一半;假如你们输了,$25000只能是你们赔款的零头。所以,无论输赢,现在以$25000和解,都是你们的最佳选择。
真让人郁闷。是坚持下去,还是选择和解?我们有点动摇。
四、录口供
时间一晃到了12月初,对方律师申请了对我进行口头取证(Desposition),就是录口供。因为疫情,这次取证选择视频会议的方式。
我们的律师犯了第二个错误,他没有对我讲解什么是口头取证。我以为那天就是和对方律师面谈一下。
口头取证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有法院的书记员进行记录。那天早上,对方律师老卡、我的律师A、法庭书记员、加上我,同时登入zoom。
口头取证开始。上来第一件事就是老卡让我举右手,宣誓我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
这里要说一下老卡。
老卡50多岁,是“老卡与老莫律师事务所”的创办人,已经干了律师这行30多年。我是刚刚知道,他是“全美百佳出庭律师”,连续15年的新泽西州“超级律师”,是新泽西司法协会的前会长,美国司法协会的理事,社会头衔一大堆,经常上地方和国家电视,发表过很多文章。
他还获过民权奖,并且是某“多元化、平等和包容性委员会”的现任主席。
他这个律师事务所,有十几个律师,受理过上万个案子,有许多案子赢了上百万美元,几十万美元。
一句话总结,老卡是“金牌大律”,他的律师事务所也非常有实力。
在外人眼里,他履历光鲜,是业界翘楚。在我眼里,他不择手段,是无良律师的代表。这是后话。
口头取证开始,老卡表现的非常专业。毕竟是大律师,他问的许多问题我都毫无准备。比如“你们公司的股份是如何分配的?股权协议是哪一年签订的?每个员工的工资是多少?给员工提供医疗保险吗?你们是如何培训员工的,有录像吗?有员工手册吗?员工手册的第一版是哪年印的?……”
很多问题在我看来是和这个案子没有关系的,但是老卡提问,我就得回答。有些我还真一时答不上来。
大概一个半小时,取证结束。我长吁了一口气。虽然有的回答不是很理想,但是案子的基本事实,我都坦然地如实回答了。比如安东尼不是主管,他没有权力参与招聘的过程;比如原告从没提交工作申请材料;比如我们没人知道店里发生过那个事件。
对方律师对我的口头取证完成了。我的律师这时犯了第三个错误:他没有申请对原告进行口头取证。我催促他尽快取证,他却说等调解之后再说。
五、调解
又过了十天左右,我们双方进行了第一次正式调解。调解员是一位退休法官。我和家人商量要不要和解(settle)。后来我们决定,可以接受和解费$5000到$8000。
那时我们给律师A已经付了9000多美元的律师费,案子进展缓慢,后面还不知要花多少钱。对方要2万5,又急着找调解员settle,我们想:赔一些钱,把事情结束了也好。
调解会议那天,调解员和我的律师先上线。我把案子的事实复述了一遍。调解员问我:“你们希望以多少钱和解?”
我回答:“我一分钱都不想给。”
调解员和我的律师同时摇头,指出这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于是我说:“我们愿意以5000美元和解。我们店关门8个月,最近刚刚重新开张,生意也不好。不过我们领到了政府给小企业的新冠补贴金一万元。我们拿出一半和解,这是我们能给出的最多的金额。”
调解员和我的律师都觉得这个数字合理。于是调解员去和原告以及他的律师老卡去谈了。
过了一会儿,调解员上线,并且把原告和老卡也拉进来了。
我第一次看见了原告的脸,一个普通的老头,皮肤微黑。他的名字是白兹。
调解员对我说:“他们商量的结果是,愿意以一万美元和解。”
这个数字超出了我们原来预订的8000美元上限,但是又没差太多。我犹豫了一下,回答:“我们不能接受这个数额。”
(现在回想,我当时为什么犹豫之后又回绝了,其实还是不甘心,觉得委屈。)
我竟然在老卡脸上看见了一抹失望的表情。
不过,我又说:“你们知道,这个店是我与几个家人一起合开的。我想回去再和他们商量一下,看看他们是否同意。”
这次调解就这样结束了。
我马上和家人商量,讨论之后觉得还是接受一万美金和解吧。这个事情已经拖了一年多了,律师费也花了不少,做个决断吧。
还是觉得气愤、不甘,但是,这哑巴亏不得不吃。
我于是给律师A发邮件,说我们愿意以一万美金和解。
第二天,律师A回复,对方要一万五千美元!
至今我没太搞懂对方律师涨价的原因。也许是因为我们没有当庭同意他们的数额,过后又服软了,想惩罚我们一下?
我们气愤之余,心反而安下来。本来我们这个和解就是不情不愿,就是强迫自己低头认怂。对方既然出妖蛾子,我们就继续打下去吧!
六、换律师
下面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炒掉律师A。我们对他的工作很不满意。我们已经付了$9000多的律师费,但是他基本上只是被动地“防守”,没有给原告方任何压力。我和家人那时对美国法律一无所知,他却从不解释、说明。有时,某个文件到了最后的提交日,对方律师催促了,他才想起来,给我们发过来,让我们自己填。
他时常对我们很不耐烦,甚至当我们询问某个问题时,说过:“你们公司还有没有英语更好的人?”
我向他表达了不再需要他的服务了,于是他通知老卡,并把我也拉进邮件链。
老卡问我:“你的下一个律师是谁?”
我说:“我想自己来打完这个官司。”
老卡说:“不行。因为被告是公司,而不是个人,所以必须由律师代理。你如果没有律师,这个案子自动判我们赢。”
我说:“那我去找找免费法律援助吧。”
老卡劝我:“你们还是接受我们之前提出的$12500的和解金额吧,让律师A帮你们把收尾工作做一下,这事就结束了。”
我有些疑惑:“$12500?你们不是要$15000吗?”
原来,老卡在提出要1.5万之后,又跟律师A说:如果我们愿意和解,给$12500就行。让我们写两张支票,一张是$2500,给原告白兹;一张是一万美金,给老卡的律师事务所。
你们看看,律师A竟然连这个信息都没给我们。
我也了解到,赔偿金中,老卡是拿80%,白兹才20%。
律师收取代理费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按照小时收费,或者一次性收费。另一种是官司打完之后,按照赔偿金额分钱。我印象中一般是律师拿三分之一,原告拿三分之二。
而这个案子,律师竟然要拿80%!律师是案件赔偿金的最大受益人。
解除了和律师A的合同之后,我马上开始寻找新律师。我在网上寻找劳动法方面的律师,然后一个一个发邮件去询问。凡是有兴趣的律师,就电话交流。
我一直参加我们镇高中家长组织的一个慈善歌舞剧演出。这个演出是为镇高中的毕业生筹集奖学金,主要的筹款方式是一本广告杂志,里面是本地一些商家的付费广告。我翻看里面的律师栏目,也给其中的一两个发了邮件。
很快,我锁定了两个候选人,一个是30出头的年轻律师,对案子信心十足,觉得随便就可以帮我打下来。他的收费是$275一个小时。
另一位就是在我们的慈善杂志上登广告的本镇律师费罗先生,70多岁,他对我们的遭遇表示真心的同情。他的收费是$360一个小时。但是,他在看了我们的所有进展后,预估需要15个小时的工作量打到庭审前。于是,他提出我们一次性支付$5400律师费。如果最后需要上庭,他预计是两天,一次性收取$3600。
我们权衡半天,还是选了年轻律师。一是觉得他冲劲儿十足,信心满满,二是觉得他便宜。
七、律师B
很快,我们就发现自己的决定是错误的了。
这位律师B虽然每个小时的费用是$275,但是他每个电话,每个短信,每个email都要算时间收费,光是复习我们之前的各种文件就花了几个小时,要了我们不少钱。
而且,他对案子的信心直线下降,不断对我说:对方的律师很有实力,很有经验。
现在想来,估计是他查了老卡以及他的律师事务所的情况,被吓住了。
我当时并不知道老卡是那么牛的律师,所以我有点不舒服:这么个事实清楚的案子,你都没怎么打,怎么能泄气呢?
律师B跟老卡谈了一次,然后跟我说:他们那边很愤怒,对你们很不满,坚持要以$25000元和解,绝不还价。
我无语:你这谈判技巧也忒差了吧!赔偿金直接被你谈翻倍了。
然后,律师B就不断催促我提高和解金额,让我出两万美元和解。
我简直想骂人:你一开始不是信誓旦旦地说这是个小case吗?说你分分钟就能搞定。怎么现在成了个棘手的案子?
然后我们不断收到他的账单,一个月下来,账单已经快4000美元。案子不光没有进展,而且大大倒退了。
我果断叫停,把他给炒了。让他再折腾下去,这钱就是无底洞了!
我马上回头找到本镇的那位老律师费罗先生,和他签了合同,一次性付了他$5400。
这是我在这个官司中做的最对的一件事!
八、审白兹
费罗先生接手后,从前面两个律师那里拿来所有的材料,赶紧填报并上交了一份马上就要逾期的文书。然后就是向对方提出口头取证。对方也提出向我的两个员工口头取证。于是,两边把时间凑了凑,定在了2021年4月初的一天。三个口头取证放在一起,只需要请一个法庭书记员就可以,能省点钱。
口头取证的前一天,费罗先生通过视频对两个员工进行了“培训”,主要就是解释口头取证的大概程序,让他们心里有些数。
对比我当初懵懵懂懂去录口供,费罗先生显然办事非常严谨,也是真心替我们着想。
口头取证依然是视频会议的形式。回答问题的人必须自己呆在一个房间里,周围不能有人。我和原告白兹可以登入视频会议旁听,但是不能说话。双方律师都在场。
老卡先询问安东尼。安东尼来自非洲加纳,50出头,在我们店干了十几年了。他从来没被律师录过口供,有些紧张。他可以说是这个案件的关键人物。所以老卡对他没有客气,有些问题让安东尼无法招架。
“你结过几次婚?有几个孩子?交过税吗?是如何报税的?公司给你报税吗?有过现金补贴吗?……”
安东尼那个时候的头脑一定是一片空白,一些问题只是本能地反驳和否认。
老卡的目的就是击破对方的心理底线,慌乱之下露出破绽。好在安东尼在关键问题上都如实并且肯定地回答了:我不认识这个人,不记得他在那天来过,我也没说过那样的话,我不会说西班牙语,我也从来不是主管。
我们的另一个员工是20出头的小伙子艾尔多。他的家庭来自波多黎各,所以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他的口供还算顺利。他非常肯定地证实:他从没听见安东尼说过西班牙语,安东尼也从来都不是主管,他也不认识原告,对他没有印象。
老卡对两位员工的问询完毕,我们的律师费罗先生,开始问询原告白兹。我们事先给费罗先生准备的许多问题也派上了用场。
一问之下,我们都有些震惊。
白兹说他每几个月来我们店一次,每次都是找安东尼,让他打折。那天,他来我们店想看看有什么新东西,发现门上的招聘启事。他觉得自己如果被聘用,就可以拿到员工折扣。于是他径直走进去,对安东尼问:“你能雇我吗?”安东尼回答:“你太老了”,还加了一句西班牙语“太老”。他就离开了。
白兹说他当时没有提高声音、没有争吵、没有找店主,没有索要工作申请表。他也没有事后回来抱怨,或者要求见店主。
白兹说他在老婆的杂货店帮忙,已经做了七八年,从来没有出去找过工作。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他依然在老婆的杂货店工作,也没有找工作。
他一直在领社安金。
也就是说,他的财务状况,并没有因为这件事而有丝毫改变。
费罗先生又问他:“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你有没有失眠?”
“没有。”
“有没有吃药?”
“没有。”
“有没有看过心理医生和精神科医生?”
“没有。”
也就是说,他的精神状况也没受到影响。
最精彩的地方到了。
费罗先生询问他有没有过其他诉讼。一问才知道,白兹曾经8次起诉他人,全部和解。其中六次是起诉他的两个前雇主,每个雇主各三次,不偏不倚。
8次和解,每次白兹拿到的赔偿金,从七千美元到三万美元不等。
我简直目瞪口呆。
我们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是被碰瓷了。
现在我们知道,自己是被惯犯碰瓷了!
白兹甚至从来都没有走到录口供这一步。每次都是早早就和解,然后回家数钱。
我们还了解到一个重要信息。费罗先生问白兹:“你3月份声称自己遇到了歧视,12月份才起诉。那么,你是什么时候找的律师呢?”
“大概事情发生后一两个星期吧。”
“那为什么要等9个月后才起诉呢?”
这时老卡突然大声说:“反对。这是我们与客户之间的隐私。”
老卡那道貌岸然的面目下隐藏的丑恶,这时终于露出一角。
老卡等了九个月才提出上诉,是因为一般店里的监控录像都是自动覆盖,监控数据只保留几个星期。我们店的录像数据就是大约两三周覆盖一次。
九个月,足够抹去监控数据,也足够抹去人们的记忆。除非是什么特大事件,否则谁能记得九个月前说的话,做的事呢?
所以,查无对证! 白兹的话就是唯一证词。
九个月,又足以让赔偿金滚动到一定数额。我想,他们的逻辑大概是这样:你看,因为你们的歧视,白兹先生失去了工作机会。来算一算吧,假如他一个月的工资是两千,那么九个月就是一万八千。他光是薪水就损失这么多,再加上精神损失…..。
为了保障客户的利益最大化,律师可以使用不同的策略和方法。但是,我们这个案子,律师要拿赔偿金的80%。所以,这是由一个碰瓷老手与无良律师共同搞出来的针对我们的诬陷。
口供录完,我们都很兴奋。费罗先生说:“今天对于你们来说,是美好的一天。”
录口供的费用包括律师费和法庭书记员的费用。我由于已经一次性支付了律师费,所以只需要支付法庭书记员的费用。费用是根据口供的长短决定。我只需要支付审问白兹的费用,$231。
老卡那边要付我和两个员工,一共三份口供的费用,特别是对我的询问比较长,应该总共花了一千元以上。
对方的底,通过这次问询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我们对这个官司的走向更有信心了。
九、简易判决
下一步,就是庭审了。由于疫情,法院的案件挤压很多,庭审日定的是一年后的2022年4月。
在等待庭审的一年里,法院又召集两个律师进行了几次调解。我们象征性地说了和解金1、2千美元,对方没有同意。
为什么费罗先生坚持让我们每次都出一个象征性的数字呢?因为他说,这可以让法官对我们有个良好的印象,认为我们一直在积极地解决问题。而对方不同意接受赔偿,代表他们是比较难缠和贪婪的一方。
转眼到了2022年。我们的庭审日期被法院推迟到六月份。我们和费罗先生开始商量是否提交“简易判决”的申请。
简易判决(Summary Judgment)是要求法官根据书面材料对案件进行直接判决,免去庭审过程,节约大量的法庭成本。不过提交简易判决也要准备资料,特别是对方如果提出反对,这边还要应对。
费罗先生说如果我们这边申请简易判决,他就一次性收取$1800。
他说申请简易判决,对于我这边唯一的坏处就是这笔额外费用,而好处却有很多。万一法官同意简易判决,判我们赢,我们就不用上庭,也不用支付庭审那笔律师费。假如对方提出反对,他们必须提交足够的理由说服法官,那么我们就知道了他们的全部底牌,可以为庭审做好准备。
我们同意费罗先生的建议。简易判决的申请在四月份初发出了。四月底,老卡提出反对,提交了一百多页的文件,里面大部分是我们三个人的证词,以及很多法律条文,坚持认为他们的起诉是正确的。
费罗先生又根据他的回应进行书面反驳。
5月13日,法官和两个律师开会,讨论简易判决申请。两个律师争执不下,最后法官说:还是由陪审团决定吧。
简易判决这条路失败了。
费罗先生说他私下与法官沟通时,法官对我们是同情的,但是他还是把球踢给了陪审团。
在美国,90%左右的民事诉讼都以和解或者撤案告终。我们这样一个小案子,竟然打到陪审团,恐怕是千古奇闻了。
费罗先生告诉我,我们这样的案子,陪审团一般由6到8人组成。因为是民事诉讼,判决允许有一票不同意。换句话说,作为被告的我们,只要争取到两票,就赢了。
只要两票就赢,我们的信心大增。
十、庭审改期
新的庭审日期是6月20日。我二女儿的高中毕业典礼是6月22日,加上两个律师那天都有事,所以提交了推迟庭审的申请。
对了,对方的律师不再是老卡,而换成了他们律师事务所的一位女律师。
庭审日期推到7月,又推到10月,又推到12月19日。
我和费罗先生保持密切联系,经常通话讨论案子,每次也会说些闲话。他对我的了解逐渐深入。
有一次他说:“新,你的简历非常令人难忘。我会想办法在庭审时,引出一点相关话题,让陪审团更了解你这个人。”
12月19日那天早上,我准时到了博根郡法院指定的法庭,背着一个大包,里面有厚厚的材料,还有一份法庭陈词。
我花了不少精力写这份陈词,还让我那文笔很好的女儿为我润色。我要站在陪审团和法官面前,把这几年的经历的一切都说出来,要求法律公正判决。
对方女律师也来了,30出头,一身正装,拉着一个公文箱。
法庭里坐了几十号人,都是律师和当事人。法庭工作人员开始一个案子一个案子地点名。有几个案子在最后时刻达成和解,工作人员就让他们回家了。需要继续审理的案件,就开始分配法官。
第一轮我们没有分到法官,我们和其他剩下的人被领到另一个房间,继续等待。
第二轮我们又没分到法官,工作人员让大家回家,等待新的庭审通知。
折腾了好几个小时,就这么无功而返了?
费罗先生说这很正常。有时候要来来回回好几次才能够分到法官。
那天晚上发生的一件事激怒了我们。
这个案子,白兹是原告,我们公司是被告,我是被告代表。我们被告方的证人有两个,就是我们的两个员工安东尼和艾尔多。
原告方上交的证人名单也有两个,也是安东尼和艾尔多。
为了确保证人出席,一般律师会给证人一份上庭通知书,必须送到证人手中。
安东尼和艾尔多就是我们的员工,我只是每次通知他们一下,准备哪天上庭。
但是,比较古怪的是,对方律师每一次都给安东尼和艾尔多发一份正式的律师函,要求他们上庭。
从录口供那次开始,他们就收到这个信。庭审时间改了四次,两人也各又收到四次出庭通知。每次送信的都是五大三粗的汉子。送达时间有时是早上八点之前,有时是天黑之后。
安东尼住在美国犯罪率最高的城市帕特森,又是个黑人移民。送通知的大汉砰砰用力敲门,人不出来就一直敲,每次都有左邻右舍出来张望。安东尼一家吓得要死。
艾尔多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有一次送信的人连门都没敲,直接推门进去把通知给他妈妈。
他妈妈差点吓出心脏病。
12月19日这天晚上,安东尼又听见砰砰的砸门声,过了很久也不停息。无奈,住在他家的表弟去开门。又是一个大汉,手里端着一个托盘,上面是几张纸,正是要求安东尼在19日早上出庭的通知!
可是,当时已经是19日晚上了,而且,白天的开庭已经取消了。
估计老卡的律师事务所是雇用了专门投递这类信件的公司来送庭审通知。阴差阳错,本应提前几天送达的文件,在开庭时间已经过了之后才送到。
我把这些事情告诉了费罗先生,他当即给女律师发了一封言辞严厉的邮件,指出他们的这种做法是对证人的威胁和骚扰,是为了吓唬证人,让他们不敢出庭。费罗先生说,这两个人本来也是我们的证人,是一定要出庭的,你们明明知道这一点,为什么还要通过这样的手段送达通知书?这个案子本就是无中生有,是诈骗,你们赶紧撤案为上。请停止对证人们的骚扰。
一针见血。老卡为了迫使我们和解,真是使用了下三滥的手段。
从那以后,果然再无人给这两个员工递送出庭通知了。
2022年就这样过去。新的庭审日是2023年2月26日。那天,我依然是准时来到法院,费罗先生和女律师也来了。
又是重复了和上一次一样的程序,又是漫长的等待,又是没有分配到法官。又被打发回家了。
我听到女律师对费罗先生抱怨:“我家住的太远,每次过来单程就要一个半小时。这案子我希望他们能和解。”
我听了之后幸灾乐祸,活该,给了你们多少次机会你们都不抓住。现在我们都磕到庭审了,想和解,做梦去吧。你就跟着折腾吧。
对于我来说,已经给费罗先生付完庭审的费用3600美元,我一点压力都没有了。法庭离我和费罗先生的家又不远。我多跑几次都没关系。
而且,我跟费罗先生说了,假如庭审我输了,我一分钱都不给他们,我继续上诉,哪怕打到美国高级法院我也要坚持。
下一个庭审日是4月19日,我说不行,我要回中国。因为新冠我已经三年半没有回去,这个行程是非常重要的。
4月底到5月底,我回国呆了一个月。这时新的庭审日期改在7月11日。
7月10日晚上,费罗先生给我打电话,说女律师要求延迟开庭。她怀孕5个月了,是双胞胎,医生不让她长途开车。
庭审再次推迟到10月23日。
10月中旬,安东尼递了请假条,10月26日他要休假。我想起庭审这事,于是联系费罗先生,问他能否申请再次延期。费罗先生说,这一次法院已经给我们这个案子指派了一位女法官,而且按照常理,这个案子庭审的时间不会超过三天,最好不要再延期了。
我同意了。该来的总要来,就这样吧。
于是,一场精彩的庭审大戏,在延期了八次之后,终于就要上演了。
十一、选陪审团
10月23日,星期一,天气晴朗。我头一夜出乎意料地睡了一个好觉。9点到达了法院的331号法庭,被告白兹和他的新律师已经坐在原告席上。原来的女律师因为怀孕已经退出,这一次的新律师是个300多磅的大胖子马克,30多岁。他家在宾州,距离这里单程2个多小时。
法庭的房间不大,除了白兹和律师,我和费罗先生之外,还有这个案子的女法官玛丽,法庭女秘书,以及一个法警。
这一天主要的任务就是挑选陪审团成员。我们要从50个候选人里选出七人。
这50人其实已经经过第一轮海选。在第一轮的时候,除了要确定他们年满18岁,是博根郡的居民,没有犯罪记录外,还要剔除那些曾经来过我们店,或者认识原告、被告,两个律师的人。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参加了第一轮海选。总之,这50人都是过了第一关的。
法庭里有大屏幕,对候选人的面试是采用视频会议的形式。先是50名候选人全部上线,玛丽法官介绍各种规则、程序和注意事项,并把候选人们需要填写的问卷从头到尾读了一遍。然后让我们四人在众人前亮相。候选人们下线,进入一个一个的面试时刻。
每个候选人都要事先填好问卷。所以法官的第一个问题往往是:“问卷上哪个问题你填的是no?” 如果全部问题回答了“是”,那么就进入下一步的深入面谈阶段。
50个候选人,其中20个左右,对问卷上的某个问题说了No,即表明自己有理由不能参加这个案件的陪审过程。这20个人的理由五花八门,大部分是不能连续参加三天的庭审。比如自己生病、要照顾孩子、要照顾老爸老妈、刚刚工作、家里要换锅炉、是老师,是大学生,不能缺课、是护士主管,正在培训新护士,等等。
玛丽法官挺好说话,都同意他们的请求了。
候选人里有一个律师,跟马克的律师事务所有好多案子的纠葛,所以退出了。
有四个人,其实可以是我们最有力的支持者。他们虽然只看到这个案子最简单的介绍,已经直接站边我们。
有一个在建筑公司工作的西班牙裔人,非常反感现在随便乱起诉的现象,而且认为年龄歧视是个伪命题,太年轻太老都可以是雇主不录取这个人的正当因素。
有一个长相很精神的亚裔小伙子,看姓氏也许是华裔,他说自己的父母、叔叔阿姨都在美国开小店。“作为亚裔美国人,他们永远是被歧视的一方,而不是他们去歧视别人”。他无法保持公正态度。
有一个物业公司的主管,非常气愤地说:我们公司面临无数的法律起诉,很多都是无中生有。所有的案件都和解了,从没走到庭审这一步。但是我们为此支付了大量的律师费和赔偿金,物业管理费也只能不断上涨。他说自己100%是有偏向倾向的。
另一个是住在我们镇的一个韩裔,是50个候选人中唯一来自我们镇的。他说自己不同意新泽西反对年龄歧视的法案。年龄是与身体状况等其他因素密切相关的。假如某个工作需要天天搬动80磅的东西。一个老年人来,拍着胸脯说自己没问题。即使他看上去挺结实,你敢录取他,并且让他搬80磅的东西吗?
法官也同意这四个人退出了。我和费罗先生扼腕叹息。
那些所有问题都答了yes,进入下一轮的候选人,玛丽法官会问一些问题,比如:介绍一下你自己,介绍你的家庭情况,你的兴趣爱好,新闻是从哪个渠道获得;你认为雇主应该如何招聘员工;你觉得目前美国的法律系统,是起诉的过于轻易,还是起诉的不够,还是均衡;你能否抛开种族、信仰等因素,公正地做出判断,等等。
询问的目的,是让我们双方了解这些候选人,然后选出对自己有利的陪审员。
这些留下的人里,有两个华人男士,一个是年轻药剂师,另一个在医院工作,妻子最近回北京探亲。
每当访谈完留下的人达到七个的时候,这七人就会同时上线,双方律师开始踢人。踢人不需要给出任何理由。每人各踢一个对自己不利的候选人。然后访谈继续进行,达到七人后,重复踢人过程。每个律师有六次踢人机会。
对方律师首先踢掉了两个华人,然后踢掉了所有在访谈的时候,表达如今官司太多,很多是不必要的那些人。我们踢掉三个,一个是个老太太,新冠刚好,一直咳嗽喘气,不忍心让她来受几天罪;还踢了二个20岁的小伙子。他们任何问题都回答是是是,我觉得他们太年轻,没有经过社会的毒打,看问题不一定全面。
有一个西班牙裔候选人,我有些犹豫。他是个30多岁的卡车司机,和老婆孩子以及岳父岳母住在一起。他说自己的岳父已经70岁了,依然在愉快地工作着。
最后时刻,费罗先生还问了我一句:这个人你想留吗?
我想了想,说:留下吧。
我对于老年人工作没有偏见。如果你能胜任工作,干到70岁,80岁,都没问题。
就这样,经过一轮又一轮,最后剩下7个人,双方都同意,陪审团诞生了。
陪审团5女2男。
1号陪审员,男,白人:去年大学毕业,已经工作,父亲是法官,母亲是医生。
2号陪审员,女,白人:曾经从事法律工作多年,后来改行,目前是医院的管理人员。
3号陪审员,女,白人:硕士学位,已经当了17年的教师。
4号陪审员,女,白人:一个跨国公司的部门主管,热心参与教会活动。
5号陪审员,男,西班牙裔:FedEx卡车司机,岳父70岁依然愉快地工作
6号陪审员,女,白人:硕士学位,高中教师,与父母生活在一起。父亲退休了,母亲在医院从事管理工作。
7号陪审员,女,黑人:执业护士,丈夫是监狱管理人员,有两个上高中的孩子。
从这个陪审团的组成上看,明面上我吃亏了,因为没有一个亚裔,却有西班牙裔。陪审团里也没有一个小业主。
陪审团女性居多。因为对方律师踢了两个华人男士,我们踢了两个20岁的大男孩。另外,之前因为同情我们而失去资格的那四个人都是男士。
女性可能会更同情弱者(白兹),但也可能更同情我。这一点上我们双方持平。
这些陪审员除了那个司机外,都是大学甚至硕士学历的白领。所有人的言谈举止都是理性而有素质。我相信他们的判断能力。
法官让陪审员们即使回家也不能查这个案子,不能搜索原告被告双方,不能跟其他人谈论这个案子。总之,就是不受任何外界干扰,以法庭上听到的信息来做判断。
这时,我们得到了一个非常不利于我们的消息。对方律师向法官提出申请,让我们这边不能在法庭上提白兹曾经8次起诉他人,并都获得和解金的事情。
法官同意了他的请求,因为白兹的最后一个官司是在十来年前了。法律上的确有这方面的根据,超过一定期限的官司,可以不作为证据在法庭辩论中使用。
这本来是我们杀伤力最大的一个论据。我相信只要陪审团听到白兹以前曾8次告别人,其中两个雇主被他各告三次,心里的天平就会向我这边倾斜的。
我们的杀手锏不能使用了,而我一直担心对手还有什么隐藏很深的大杀器没有露出来。
我想对方一定有什么后招,不然他们为什么要打这个官司?为什么要跟我们拼到庭审?要知道老卡是大律师,他的事务所打过上万个官司。我们这个小案子,油水真不大,他们为什么要打到现在?马克每天从宾州来上庭,光路程就是五六个小时,他们的动力是什么?
我的头脑里总是有这样的镜头:在我们的庭审中,双方唇枪舌剑,不相上下。这时,对方律师突然向法官说:我们有新的证人(证据),请法庭批准我们呈现。法官同意之后,房间的门缓缓打开,一个终极大杀器登场了……。
十二、法庭辩论
10月24日,正式庭审日,陪审团七名成员全部到场,坐在陪审席上。法庭辩论开始。顺序是这样:对方律师马克开场陈词,我的律师费罗开场陈词,然后下面是交叉询问,依次是白兹、安东尼、艾尔多、我。
这个顺序是开庭前临时调整的,对我很有利。因为我是最后一个出场。而且作为被告,我是可以听到安东尼和艾尔多的证词的。
对方律师马克第一个登场了。他的开场陈词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只不过极力想说明白兹声称的事情是发生过的,而且是年龄歧视导致了他没有得到工作机会。
费罗先生出场了,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是一场毫无意义的诉讼(frivolous lawsuit),是一个设计好的骗局。”
然后,费罗先生把所有的事实清清楚楚地罗列出来,证明我们没有任何过错。
两个律师的开场陈词结束后,白兹上场接受交叉询问。他的回答与两年半前的口供基本一样。
有几个有意思的地方。原告这边提供的证据只有一张照片,是我们店的门上贴的一张招聘启事。马克问:“你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 白兹回答:“是两天后。”
费罗先生抓住这个漏洞:“两天后你去拍照片的时候,你进店里了吗?”
“没有,我拍完就开车走了。”
“你为什么不进去跟店主抱怨安东尼做的事?”
“我害怕进去后,他们会叫警察抓我。”
全场静默。我能想象得出,每个人的脑子里都是一串问号。
费罗先生又问:“他们为什么会叫警察抓你?”
“因为他们拒绝了我的工作申请。”
这些话已经是毫无逻辑,胡言乱语了。
但是,他自己两天后偷偷回去拍了招聘启事然后溜走这件事,恐怕让陪审员们都要想一下,是不是他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是想起诉我们。
费罗先生又问:“在你一生当中,肯定有过不少难过、委屈、受到伤害的时刻。那么,你比较一下,那天在店里发生的事,和你一生中其他伤害相比,可以排在第几位?”
白兹回答:“那件事是我那一天中最难过的时刻。”
费罗先生重复问了两遍,白兹的回答不变。
白兹还说:“他当时如果跟我道个歉,我就没事了。我也就不会今天坐在这里了。”
他突然喊了一声:“我要正义!” 然后眼中似乎有了泪光。
我浑身恶寒,又有些愤怒。假如他说的是真的,那天的确被安东尼回了一句“你太老了”,可是,按照他的说法,这一句话对他造成的伤害是微不足道的,是一句道歉就能弥补的。那么,你为什么要起诉我们,为什么要把我们拖入这一场长达四年的官司之中?
你还有脸喊:“我要正义”。我们的正义又在哪里?
中午休息的时候,我和费罗先生出去吃饭,我们两人都觉得白兹的证词给他减分了。
下面就看两个员工的表现了。
下午安东尼第一个被询问。证人是不能参与前面的庭审的,所以他们不知道两个律师的开场白和白兹的证词。
马克刚刚问了安东尼几句话,当问到你是否认识我身边这位先生时,安东尼回答不认识。这时白兹突然向安东尼发难,质问他为什么不记得自己。玛丽法官马上厉声制止:“你不要跟证人讲话,不要干扰证人作证!”
我望向安东尼,他气的眼冒火星。他也被这四年的诉讼拖累的够呛,还被送信大汉夜里砸门。我心里一紧,担心安东尼被激怒。玛丽法官已经高声让法警过来,让法警站在白兹面前,阻断白兹的视线。
玛丽法官然后柔声安慰安东尼:“你不要看他,你可以看我,看律师,或者看陪审团。”
下面的询问没有太多“意外”。某个事情安东尼在录口供的时候说“我不记得了”,这次回答是“我不知道”。于是,马克非要说安东尼的回答不一致,“我不记得了”和“我不知道”不是一回事。安东尼说是一回事。两人纠缠了半天。玛丽法官隐隐有些不耐烦:“安东尼说的有道理。这个话题翻篇吧。”
艾尔多的作证要简单得多。两个律师都没问太多问题。
终于轮到我上场了。我的心情异常平静。事先想象的“大杀器”根本不存在;白兹的证词和现场表现都比较差;而我们两个员工没出大问题。
这一天,这一刻,我已经准备了快四年!
费罗先生先问了几个关于公司的基本问题,然后他问:“你是在哪里出生的?”
“中国辽宁。”
“你的教育背景是什么?”
“我毕业于北京大学,后来在中国人民大学拿到硕士学位。专业是社会学。”
“你在美国也读书了吗?”
“是的,又拿了一个硕士学位。”
“你在中国工作过吗?”
“是的,从事妇女和儿童的研究工作。”
这时我反应过来,费罗先生这是给我立人设呢。
我和费罗先生从来没讨论过庭审上如何问答。我没想到他一上来就问这些问题,还问的这么直接。
他又问:“你平时都做些什么?从事慈善活动吗?”
“是的。疫情期间,我们店关门了。我组织了很多PPE的捐赠,捐给医院、老人院、警察局、消防局等。那时,中国人捐了很多这类东西。”
“什么是PPE?”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就是口罩、手套、洗手液什么的。”
“你提到捐给医院?”
“是的,医院是捐赠的大头。”
陪审席上有好几个人在医院工作,或者有家人在医院工作。所以,我想费罗先生特意强调了一下医院。
“你听说过心愿单项目吗?”
我都没想到费罗先生递梯子递的这么明显。
“实际上这个项目是我发起的,是帮助那些领养了中国残疾儿童的美国家庭。”
“你的文化有什么特点?”
“我们的文化特别尊重老年人。每当有年纪大的客人来我们店,我都给予他们特别的照顾,从他们身上,我可以看到我的父母,看到未来的我。我们的员工也会给他们提供帮助,比如帮他们把东西搬上车等。”
好了,立人设的阶段到此为止。
现在回头想想,我还觉得有点意犹未尽。因为事先没有准备,所以我的回答特别简单。其实可以说的事情还有很多,感觉我这个人设还不太丰满。
但是,也许这给了陪审团一个谦卑和诚恳的印象吧。
马克那边没有给我太多挑战性的问题。这件事情,我们从头到尾都不知道,所以,我一切实话实说即可。他曾经想抓住某个文件里我的一个小纰漏来质问我。玛丽法官问他:“你问这个问题的意义是什么?这个小纰漏无关大局。”
其实那个纰漏我完全可以解释清楚,但是马克没有继续追问下去。
而我,在回答两个律师的提问中,不断贯穿这样一个信息:我们这个小店,是这个mall里存活时间最久的店,已经快25年。这25年,我们没吃过一个官司。我们生存的技巧,靠的是小心谨慎,靠的是与人为善。
问询全部结束后,陪审团离开。费罗先生向玛丽法官提出撤案申请。他说:“从今天一天的庭审结果来看,这个诉讼是毫无事实根据的。”马克反驳了这个提议。玛丽法官犹豫了许久,还是决定明天继续开庭。
那天晚上,我忙到半夜,修改自己的法庭陈词,还给费罗先生的最后陈词提了好多建议。
十三、判决日
10月25日,判决日。九点,法官召集两个律师,以及我和白兹,讨论她拟出来的陪审团指示(Jury Charge)。她把这个案子的所有信息罗列出来,配上所有相关的法律条文,还加了几个例子,目的是让陪审员们理解如何做出公平的判决。
两个律师都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马克提出,将“原告要求经济赔偿和精神赔偿”这句话中的“经济赔偿”划掉。
因为原告的所有证词已经表明他没有受到任何经济上的损失,这时候再提经济赔偿,难免会让陪审团产生“这个人很贪婪,一切为了钱”的想法。
这次陪审团是由7人组成,所以需要原告拿到7:0或者6:1。
玛丽法官修改了陪审团指示之后,拟出了裁决投票表(Verdict Sheet)。这个裁决投票表上有三个问题。
1、原告白兹先生是否被XX公司拒绝了申请工作的机会?
下面有两个选择,“是”和“否”。
假如有六个陪审员以上都回答“是”,那么进入下一个问题。
2、原告白兹先生是否遭受了XX公司的年龄歧视?
假如有六个陪审员以上也都回答“是”,那么进入下一个问题。
3、你认为应该给白兹先生多少赔偿?请写下具体金额。
我和费罗先生都觉得这个投票表设计的不错,相当于给了我们双重保护。即使我们输掉第一轮,还有第二轮兜底。
马克马上表示反对。他说第一个和第二个问题可以合并。白兹是因为年龄歧视被拒绝了工作机会。
玛丽法官说:谢谢你的建议,但是我坚持我的设计。某人被拒绝了工作机会,这背后的原因可能有很多。细化可以让判决更准确。
11点,7名陪审团成员全部坐在位子上。两位律师面对他们,开始最后陈词,希望能再使劲一下,把陪审团拉到自己这边。
费罗先生再次重申:这是一次恶意起诉,是一次欺诈。他一条条摆事实指出这个起诉是多么离谱。他还说:“这位女士,Xin Luo, 有两个硕士学位,做过无数慈善工作,帮助过那么多需要帮助的人。她的文化背景,是对老人非常尊敬;她的员工,对她非常忠诚。你们觉得,她会自己做出,或者教唆员工做出,年龄歧视的事吗?”
他还说,这个案子,历时四年,浪费了很多公共资源。他恳请各位陪审员,在判决表上填写“否”。
接下来是马克的最后陈词。说实话,他讲的还不错,能让他发挥的空间并不多,他尽量说的真诚。他说:白兹先生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尊严而战。请大家填写“是”。
两位律师的最后陈词结束后,玛丽法官开始给陪审团详细讲解“陪审团指示”以及“裁决表”,她告诉大家:用你们的心,你们的直觉,你们的判断,全面考量所有的证据、证词。
我始终没有机会在陪审团面前慷慨陈词,看来白准备了。
这时,时间已经是12点10分。而法庭的午休时间是12点半到1点半。玛丽法官让陪审团进入另一个房间进行评议(deliberating)。她说:你们先评议一会儿,然后休息一个小时,1点半继续开始评议。你们有了结果,就按一下房间里的按钮。
最紧张的时刻到了!
由普通人组成的陪审团制度,在公众的心目中向来褒贬不一。很多人觉得后果难以把握。这几天的庭审下来,我感觉我们这边发挥的不错,但是,我还是有些紧张。
我出去上了个洗手间,就走回法庭里坐下。这时我看见秘书桌子上的灯在一闪一闪地发亮。我想起法官说的:你们如果有了结果,就按一下按钮。我的心里升起期盼。
过了一会儿,玛丽法官走了进来,她宣布,裁决结果已经产生。
于是,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我们赢了,而且赢得干脆利落,赢得痛快淋漓。第一轮的问题,我们就以7:0拿下。后面两轮问题根本用不上。
费罗先生参与的案子中有100多个到了最后的裁决。他说我们这个案子是陪审团出结果最快的一次。许多案件的评议时间都是几个小时,甚至几天。而我们这个,不到十分钟。
也就是说,7个评审员,在走出屋子那一刻,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他们全部在裁决表的第一个问题那里,回答了No。
7个陪审员,没有一个华裔,甚至没有一个亚裔,还包括了一个认同老年人工作的西班牙裔,他们全部支持我们!
这个胜利,太漂亮了!
我和费罗先生紧紧握手,又把消息通知了店里,引起大家一片欢呼。
压在大家心头四年的大石被瞬间挪开,让人无比轻松。
十四、信心
很多一直关心我们这个官司的朋友们听说这个消息,都表示祝贺,都说:“对美国的司法程序和陪审团制度又有了一些信心。”
而我,在慢慢平静下来之后,才觉得这个案子和这个结果的意义,非同一般。
在美国有很多恶意诉讼,有很多碰瓷和诬陷。而多数公司、企业甚至个人,为了避免漫长的应诉过程,高昂的律师费用,以及不确定的后果,往往选择和解,花钱消灾。
这也就助长了那些碰瓷者的气焰,让这类的官司越来越多。不少企业和个人都深受其害。
我们这样一个小企业,由少数族裔组成,被人恶意诉讼,而对方的代理律师又非常有实力,咄咄逼人。
在这样不利的情况下,我们硬是挺到陪审团阶段,并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这个结果对于和我们一样被欺负的老实人和小企业,是一个莫大的鼓舞;对那些碰瓷者和在背后推波助澜的无良律师,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我们的所有朋友和家人都知道这个案子;50个陪审员候选人知道了这个案子;7个陪审团成员从头到尾跟了庭审过程;法官、秘书、法警都熟悉了这个案子;最后一天还有两个年轻的实习生观摩了整个过程……。
这些人,会告诉他们的亲朋好友,他们的亲朋好友,还会告诉其他人:有这样一个案子,竟然打到陪审团,竟然大获全胜…..。
原来,小人物也可以不与邪恶和解,也能迎来公平和正义。
我们这个案例,也许会被玛丽和其他法官反复使用,作为后面判案的一个根据。
如果能够通过这个案子,促进一些法律法规更加完善,那就更不枉我们这四年的坚持。
而对于我们来说,假如当时同意以一万美元和解,加上已经付的9000多元律师费,我们花出去2万美元,换来一辈子的窝囊和气愤。我们会怀疑美国的司法制度,怀疑世间是否有公道。
现在,我们总共花了2万5千美元,赢来了一个碾压性的胜利。我可以一辈子都自豪地夸耀:我曾经打败了很牛的律师,并且在陪审团那里赢了全票支持。
给那些和我们有类似遭遇的朋友一点建议:
1、很多时候,从节省金钱和精力的角度来讲,和解的确比较“划算”。如果想和解,越早越好,不然律师费越来越多。
2、找个好律师。律师太重要了,找一个对你的处境真心同情,总设身处地为你着想的人。我很幸运,最后遇到费罗先生。
3、争取让律师给一个一次性付款的价格(flat rate)。这个案子我们最焦虑的时候,就是前两个律师不断寄来账单的时候。看见钱哗哗流出去,心痛;又对后面的花费无法预测,感觉心里没底。
当费罗先生接手后,费用都事先支付完毕,我们心理压力小了很多。庭审费,费罗先生一次性收了$3600。实际上庭审花了三天,之前还有两次去法院呆了半天又被赶回来,所以就是五天,还有八次延期,以及中间很多次电话、邮件沟通,和法官开会。费罗先生还要花时间准备庭审。我算了一下,整个庭审过程他至少花了40个小时,按照$360一个小时,已经快1.5万美元。
想象一下,如果我不是一次性支付了庭审费,而是按照小时付钱,那么,看见这么多费用每天不断叠加,心里也是会很难受的。
4、要对陪审团制度有信心。我参加了整个陪审团的筛选过程,我觉得还是非常严谨和公正的。而且不要低估人性的力量。即使是普通人,心中也有一杆秤。我的陪审团以史上最快速度,给了一个7:0的结果,说明人心向善,邪不压正。
打官司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事,希望没有人能遇上我们这样的事。不过一旦遇上,也只能面对。也许我们的经历,能给你们一点启发和鼓舞。
正义虽然会迟到,但不会缺席。
我们用四年的时间,等来了一个正义的结局,并给很多人带来了对这个社会的希望。
2023年10月31日,万圣节,我和费罗先生一起,向新泽西高级法院提交了要求原告赔偿我们的律师费的申请(Motion for Bad Faith Attorney Fees)。
费罗先生说,他打过这么多案子,还从来没遇到过被告赢了之后,把花掉的律师费要回来的,他也没听说过周围有这个事情。
又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法律上,的确是有这样的条款,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却很难实行。
但是,如果不去惩罚这些碰瓷者和无良律师,他们就会有恃无恐,就会一直钻法律的漏洞。
我不知道我们的申请是否被批准。我想,如果法院拒绝了我的申请,我会向众议员、参议员写信,我会通过媒体,争取公众的支持,来促使法律的改变。
不能总是老实人受欺负!法律也不能成为坏人的保护伞!
希望下一个好消息也能到来。
追求正义的道路比较曲折,但是,胜利的果实也格外甜蜜。
转载于:七彩娘娘
Views: 0